书名:《义理·考据·辞章:中国传统学术的综合研究》
出版信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
内容简介/前言:
本书是一部从文、史、哲多学科角度综合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论文选集。
文学方面,作者以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中国文学早中期诗歌和小说的特点、中古玄学社会思潮与文学的关系、佛教对中古文学形式的影响等。史学方面,作者执守于传统考据学的方法,对墨翟、吴起、环渊、何晏、谢灵运、段业等的生平事迹进行了新的考证。哲学方面,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圭臬,阐述了中国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思路;其次是对中国禅宗哲学思想的源头和中国哲学的几个重要的概念范畴及学术思想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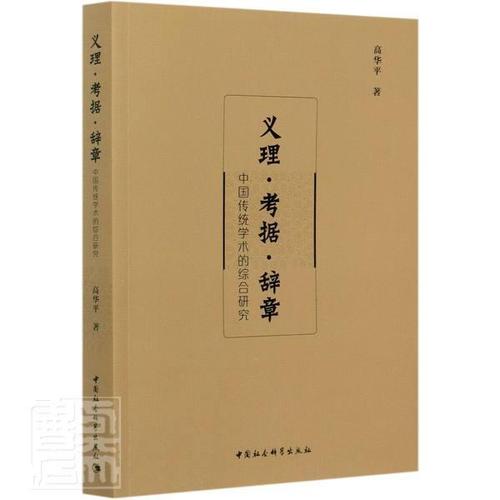
附:《义理·考据·辞章:中国传统学术的综合研究》自序
中国的传统学术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并没有现代学术中普遍存在的学科划分。它既没有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对的“人文学”概念,更没有今天“人文学”下的哲学、历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划分。中国最早的学术分科,应该是为了教学而形成的“六艺”(“大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小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春秋战国之际,孔门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论语·先进》)四科之分,墨家有“谈辩者”“说书者”“从事者”之别(《墨子·耕柱》)。至汉代,学者因刘《略》班《志》的图书“六略”之分而论学术;魏晋以往,则多主经、史、子、集“四部”。直到清代,以“四部”该中国传统学术仍为通例。但就人文学科而言,则又或以义理、考据、文章三目概之。
近代以来,“中学”与“西学”、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既从此划界;而在人文学科内部,则又有文学、历史、哲学、政治、伦理等更细的学科的划分。这无疑给中国学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延至今日,分工日细,中国的文、史、哲各科,皆既有依时段而划分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各朝之“学”,又依各学科关系而形成的各种原理之“学”,还有以专书专人而命名的各种专门之“学”,如“老学”“孔学”“庄学”“龙学”“红学”等等。分而又分,细之又细,穷年累月,“巧历不能止”。
近代以来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应该说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现代中国“人文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学科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不能否定的。但由于今天的中国和人类社会都正处于深刻的历史变革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及由此而带来的人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还有人文学科自身的缺失,都给其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困境和挑战。
经济的飞速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给传统的以文、史、哲为主要内容的“人文学”的发展带来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它既造成了传统“人文学”的日益边缘化,也带来了对传统“人文学”及其成果的有效性和社会价值的不断质疑。
但更大的危机可能来自“人文学”本身。当前中国“人文学”自身的困境,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人文学科的的细分,在文、史、哲划分之后,又有按时段、地域、流派等的划分,以及由这些学科交叉而组成的新的学科领域,这样虽然带来了“人文学”研究的深入、深刻和专精;但这种分科过细的研究也给“人文学”中的文、史、哲各学科发展造成明显的局限、甚至阻滞。
其表现之一,是这种研究使我们在某一领域的研究很容易达到某种极限或“瓶颈”。《庄子·天下篇》记当时“辩者”的辩题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所谓“万世不竭”,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能的,但实际上由于受人的观测手段和实验工具的限制,这又是不可能的,必然会使我们在某一领域的研究很快会达到某种极限或遇到“瓶颈”。
其表现之二,是它使我们传统“人文学”中的文、史、哲各学科研究越来越越像机械和技术的工作,失去了传统学术所孕含的人文价值。例如,在当今的古汉语、古文字学研究,如果研究“汉字文化学”会成为另类,它只要“认字”,最好是通过计算机进行“图像识别”,传统的“由字通其词,由词通其道”学术道路基本被弃置不顾。又如文献学,现在似已变成了追求电子文献检索的工具,与章学诚所提倡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距离越来越远。
同时,对中国传统“人文学”的这种精细化的分科,还极大地破坏了传统“人文学”具有的学科标准、学术规范与学术生态。中国传统学术由“小学”通“经学”,再由“经学”通“史学”的治学路径,几乎再也无人提及,各学科的规范和准则荡然无存,故出现了数百、乃至数千人云集的所谓学术大会,各种文、史、哲经典被随意解读,“宏论”骇人听闻。
在当前中国的学术语境下,该如何进行传统“人文学”中的文、史、哲研究呢?我认为,学习和借鉴西方在内的各种学术经验固然是必要的;但由于中国“人文学”中的大部分内容多属于中国传统学术的范围,所以学习、借鉴和回归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就显得特别需要。
对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回归,大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学术与文化的界限。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传统学术是明确区别于一般的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它的目标是要完成传之久远的“名山事业”,属于所谓“大传统”或“精英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从事的“人文学”是“学”或“学术”,而不是一般的人文活动或一般的文化(普及)工作,更不是所谓的文化传播。“学术”可以是广义的“文化”的一部分,但却是其中的特殊部分,它是专门的学问。因此,我们所说的文学、历史和哲学,它与一般的所谓文学创作、史书编撰或哲学思考是完全不同的。它真正科学的名称应该是“文学学”、“历史学”、“哲学学”等等,它们是研究文学、历史和哲学的专门学问。这种划分,一是可以明确“人文学”自身的科学性,增强其人文实证主义的成份;二是可增强人文学学习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真正做到循序渐进,有章可循。中国传统学术其实是不缺少科学的传统的,先秦名家或“名辩家”的“白马非马”、“坚白石”之论,既是纯粹的逻辑概念辨析,梁启超等又曾以乾嘉考据学的“无征不信”和严密的逻辑之归纳与推演为真正的科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讲,回归这种传统既可以建立起中国的形而上学和人文实证主义;同时,各种“非学术”的无意义的争论也将会在“学术”领域内极大地减少、甚至消歇。
二是明确中国“人文学”的基本特点和方法。
中国现在的“人文学”虽然已被划分为文学、史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但在古代却是没有这种界限的。中国古代的一个学者,可能既是文学学者、历史学者,又是哲学学者,在面对一本经典(如“六经”之一)展开研究之时,他不会说我只是要研究中间的文学价值、历史真实或哲学思想的某一方面,而必是一种虽有侧重的综合研究。这样,可使我们的人文学研究成果,既有文学的情怀和价值理想,又不失历史实证的严谨——可使我们的人文学不至于因现代学科的精细划分而日益“碎片化”;同时,因古人的人文学研习存在由“小学”入“经学”和“史学”的循序渐进的研习程序,这样就可以有章可循,可以真正做到由“专”而“通”。
三是实现实现义理、考据、文章的结合,达到事、情、理的统一。
中国传统的“人文学”因为不强行做现代文、史、哲等学科的划分,故既不会使义理、考据和文章殊途,也不会造成事、情、理的分离与紧张。古人研究历史和哲学时,从来不缺少诗的情怀,故有大量诗(文)、史、哲研究相结合的“咏史诗”、“哲理诗”传世。历史学和哲学的研究亦然。韩愈、欧阳修、朱熹、王夫之等人可谓登峰造极。近代陈寅恪亦有“解释一个字,可作一部文化史”之说。回归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法以治现代中国的文、史、哲等“人文学”,既可以实现义理、考据、文章在现时代语境下新的融合,也可以在保持事、情、理之间必要张力的同时,实现三者新的和谐与统一。
回顾我本人的学习和学术研究的经历,所谓“向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回归”,走文、史、哲等“人文学”综合的治学之路,可以说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我的研究生以前的学历,虽然是以学习中国语言文学为主,但实际上似乎更像是有点不知道方向的“乱读书”。在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始闻程千帆先生开辟的“文学批评与考据学相结合”的诗学;得周勋初先生等诲以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大师“通人之学”的治学方法,然后略知中国传统学术本无所谓文、史、哲之畛域,义理、考据、文章相结合实为治中国文史学术之通途。硕士毕业后至武汉工作,先在华中师范大学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麾下研习中国历史文献之学,后又至武汉大学诗人哲学史家萧萐父先生门下研习中国古典哲学,益知所谓“由小学入经学而后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而后史学可信”和所谓“文、史、哲不分家”之义。由于受此种学术环境的熏染,本人亦日渐对中国传统学术之特点和方法萌生出些许的自觉,遂有向中国传统学术固有方法回归、以治中国学术之意。
以中国传统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的学术,我的具体方法,就是走以文献学为基础的文、史、哲综合研究之路。在从事任何一项研究的时候,我一般都不会局限于从文、史、哲的某一个领域展开研究,而是会先考虑这项研究中包含了哪些文学、史学或哲学的问题;前人主要是从文、史、哲中的一个学科来研究这一问题的。如果前人已主要从某一学科来研究这一问题,那么我除了进一步思考从该学科继续研究这一问题的可能性之外,会更多地尝试从其它相邻学科或多学科综合的途径展开探索,力求借助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综合的特点,从学科的交叉和边缘处寻找突破点。从中国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和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学的知识,到中国传统的“经学”和“史学”等科目,只要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能带来实质性的帮助,都是我所必须借鉴和采用的方法。例如,中国古代《诗经》四言诗体的研究,我既不会囿于传统的“经学”,也不会局限于现代文体学的观点去进行探讨,而是考虑因中国早期诗歌具体“合乐”的特点而从音乐的角度进行考察;因中国古文字(先秦“古文”)具有很强的表意功能、而从出土文献中“诗”“歌”等文字的形义来印证当时诗体的特点;到魏晋隋唐之际,我则会结合当时主要的哲学社会思潮(玄学、佛学等)进行更广泛的考察。又如,对先秦“小说”和“小说家”的研究,我并不沿袭目前学术界或以“小说”和“小说家”为文学问题的老路来进行研究,而是将其放在中国早期经典形成过程中的“经”“传”(“说”)关系的角度,对先秦的“小说”和“小说家”进行文、史、哲的综合研究(包括借助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方法对“传”“说”“知”概念或字词的解析)等。对于先秦“道”“仁”“义”“贤”“美”哲学概念的辨析,我不会局限于现代哲学对概念的逻辑分析,而是会继承中国传统学术“由字通其词,由词通其道”的思路,力求从古文字(包括出土的文字材料)的演变中,对中国早期哲学观念进行实证性的研究,以期为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找到新的突破;而如果这个哲学问题涉及文艺审美或历史事实的辨析,我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文学和历史的方法展开研究的,例如在对魏晋山水美意识的演变与当时哲学思想关系的讨论时就是如此。
对于历史的研究,我甚至执拗地认为,中国传统的被人讥讽为“豆钉琐屑”的考据之学,那应该才是我国史学的正途。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应该是不分哪些是专门的文学史、哲学史或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因为说到底,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对历史存在着的人的研究;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从来都只有具体的人,没有抽象的或纯粹的“文学人”、“哲学人”或政治学、经济学的人。所以你的历史研究,也应该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对具体历史人物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还必须是以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考证为基础和前提的。因此,我在从事文、史、哲的任何研究时,都是从以文献学为基础的历史考据为出发点的,然后才是对其进行文学的、哲学的、政治思想等领域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探讨。只不过由于我平时的兴趣于文学、哲学思想为多,故我为数不多的考据文章中,对与文学和哲学相关的人物和事件的考据为多,例如我对墨子生卒年的重新考证,对吴起、环渊、詹何、段业其人其事的考辨,对何晏、谢灵运著作的考辨。
到底应该以哪种方法研究以文、史、哲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人文学”,这恐怕并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我不过以自己的体会,尝试“向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回归”。我坚信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应该是最契合中国“人文学”研究对象的方法;并且我也坚信,自己以这种方法研究,的确解决了属于中国“人文学”的文、史、哲各学科领域某些长期悬而不决的疑案,推进了相关研究的发展(我之所言是否属实,原文俱在,有疑者可以覆核)。
这本论文集共收论文21篇,其中文学、历史和哲学的论文各7篇。论文收入时于文末注明了该文最初发表的刊物和时间,并对个别改动做了说明,但对于论文转载和收录(包括收入论文集)的情况则一律未加说明。
学术慧命,薪火相传。为了我们民族的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展繁荣、发扬光大,不论我们能力的大小,每个人都应当尽自己应尽的使命和义务。
二0一九年十一月
于暨南大学
![{{siteInfoList.info[5]}}](/_upload/tpl/05/f7/1527/template1527/images/top_logo.png)